
▲ 國內雖然流浪博士多,但因大學允許教授減少授課,反而造成學生修不到課的現象。(圖/取自Pixabay)
● 李律/國立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我有很多個身分,其中一個身分叫做「流浪博士」。這個身分,從我2015年博士班畢業,一直維持到現在。
流浪的意思,從字面上直接了解,就是「沒有固定居所」。流浪博士的意思也可以以此類推,指的是「沒有找到正式教職,只能在很多學校當兼任流浪的博士」。
我博士畢業後,當過母校的博士後研究員,也為了心愛的母校書院當過「碩士級研究助理」,也做過完全不需要博士學歷的公務員。簡單地說,我沒有成為博士階段之後理當轉換的角色: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可能我不優秀、可能我是土博士沒有喝過洋墨水、可能我研究發表太少......
總而言之,十五年前,為了大學教職而決定去念博士班,以結果論來說,還真是完全搞砸了呢......。
但是我的運氣一直很好,總會有許多貴人老師給我機會(仔細想想,我目前的人生都是靠貴人老師們的幫忙走過來的),所以這學期我有了一個新身分,是北部某國立大學的兼任助理教授。

▲某國立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薪資,以鐘點費為計。(圖/翻攝畫面)
國立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薪資 比超商多一兩倍
你或許會有點好奇,兼任助理教授薪水有多少?嗯,其實就是鐘點費,每小時700多元。
這個數字,我猜絕大多數的人,甚至包括學生,大概都不知道。俗話說「吃米不知米價」,但老實說,學生真的也沒必要知道,那個在台上講到嘴角全泡的人,他到底實拿多少錢。
那個700多元(零頭我就先去掉了,總之不會超過一杯珍奶),意思是你這學期如果開了一堂兩學分的課,那麼你這學期實拿的薪水就是:
學分數*周數*700
2*18*700=25,200
25,200不是月薪喔!是這學期2月底到6月中之間,我實際拿到的薪水。
當然學校會付我車馬費,但是是實報實銷,我一毛錢也不會賺到,而是把這些錢拿去貢獻給交通業者(在這個疫情谷底中也算好事一樁)。
一堂課一小時700,算是合理嗎?好,大概比便利商店與麥當勞多了一兩倍,但是;
我的勞動不會只有在上課而已。
我每次去大學上課,往返要花四小時通勤。
我每一堂課上課前,我需要花幾個小時不等的時間來備課、製作教材。
我每一次下課後,學生只要來問我問題,我就會留下來解答到學生滿意為止。
以這個禮拜為例,我花了兩個多小時說服一個學生,不要再遇到問題就假裝沒事繞過去,要好好直面內心的傷痛與問題,好好與它對話,而對方的頑強與否定,則好幾次令我都想要禱告呼叫任何一個可以得來速的神明了。但我又完全可以理解,畢竟我就是逃避與繞過問題20多年堅決否定問題存在的高手。
然後我又花了兩小時陪另一個學生好好談話,試圖去理出為什麼他的生命中總是覺得自己不配遇到好事、得到好的對待,聽他說生命中每一個覺得這世界否定了自己的存在的時刻,然後陪他去解開每一個曾經糾纏的結,試圖找到最原初的問題癥結。
總之,四點下課,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超過十點。
當然這些我花去的時間,我是一毛錢也領不到的。
但是我並不在乎這些付出沒有金錢回報,因為我真心喜歡教書,我真心喜歡我的學生。那些心靈交流與信任,對我來說是品質很精純的時間流逝、是付出生命中一段時間的方式裡最寶貴的一種。
不過我也同意,這種超值的「售後服務」(?),並不是要求一個老師的共同標準。
一個教書的老師,跟做炸雞的攤商、重機具的操作員、公車司機、養鴨場的鴨農、交通警察、房屋仲介、清潔隊員、uber-eat外送員......或許也沒甚麼太大的不同,他們都會有倦怠的時刻、想要放空的時候、看著眼前的對象(炸雞、生產線、打結的交通、鴨、雞掰客戶、垃圾......)感到厭煩,只剩下身體的勞動,或是在一天的情緒勞動後,對自己徹底厭棄。
老師撇開了聖職的光環,都是一個一個正常的人,有喜怒哀樂、有弱點、會說謊、有時會做卑鄙的事、有時也看不起自己。
一個對教學沒有熱情的人可以當老師嗎?不行嗎?為什麼呢?

▲ 李律指出,國立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比便利商店與麥當勞多一兩倍。(示意圖/資料照)
重研究輕教學 評鑑標準綁架教師
今(11)天我的同溫層,因為易智言導演與母校傳院的新聞而徹底洗版。
政大存在的問題,我不陌生,我試著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大學需要很多兼任老師,因為,學生沒課上。
學生沒課上,因為,專任老師的基本授課學分是一學期9學分(可能因校而異),但是行政主管職以及科技部研究、產學合作等等對學校有貢獻(要嘛帶錢進來,要嘛為學校省錢)的老師可以減少授課,很多老師減到一學期3學分,當然一個系開不出甚麼課,每堂課又有修課人數上限,導致一堆學生修不到課。
為什麼會有減授制度,就是因為,對大學來說,生財最重要,所以接科技部案子最重要、招生最重要、評鑑最重要,為了這些目標,讓老師們不要太辛苦、可以心無旁鶩做研究也是應該的,教學呢?沒辦法就犧牲吧!
為什麼老師那麼少呢?不是一大堆流浪博士嗎?有的私立大學為了節省經費,老師退休了遇缺不補,用原有師資強迫分擔,或是花前面提到的六、七百元去外面找業師來補。
國立大學則是上演搶缺大戰,一個系的三級三審制,在校內搶缺嚴重、各個派系山頭都要搶的情況下,系級審、院級審、校級審,你的人馬我打槍、我的人馬你打槍,一個助理教授缺好幾個學期都因為三級三審沒過而從缺,是稀鬆平常的事。
那這些問題又是誰要負責呢?校長嗎?主秘嗎?三長嗎?院長嗎?系主任嗎?
擔任這些職務的人,都是教授、都是學者;我並不會說因為是教授,所以他們都是聖人,但最起碼,在學校的環境裡,大多數接任行政職的教授們,都有身為學者與知識分子的學養、人品,甚至還有改造大學的熱情,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是壞人。
這些問題的出現,一路推到源頭,是大學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
台灣的高等教育這十幾年來,一直在效法美國新自由主義轉向的作法,學校資源越來越少,學校越開越多,為了搶錢、大家就只好搶破頭。
而評鑑的標準,又只偏重發表數量、數字指標、為了擠進全球幾百大的排名,而重研究輕教學(結果名次還是一直掉),藉由升等的標準綁架老師們,只能埋頭做研究,完全放掉教學(還是有很多老師仍然重視教學,但是對升等毫無幫助,純粹佛心來著),之前台大社會系李明璁老師被台大解雇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管是多麼優秀的知識份子,只要不做研究,不能為學校帶錢進來,就是廢物,不要也罷。
易智言導演指出的例子,真的只是千瘡百孔的大學制度病灶沉疴的冰山一角。

▲ 李律指出,評鑑制度使大學普遍重研究輕教學 。(圖/中央大學提供)
教師底線:不能羞辱學生
但讓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導演在他的行文中,雖然批判了政大的制度,卻把學生當作「整個結構制度的共犯」,這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前面提到的大學荒謬制度,坦白說人人都是輸家。犧牲了教學品質,學生是最直接的輸家;制度羞辱了擔任兼任教師的專業人才,這些人也是輸家。可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專任老師們、甚至是每學期為了開不出課焦頭爛額好說歹說求爺爺告奶奶哄人來兼課的主任、教授們,他們一樣好過不到哪裡去。
我可以想像導演懷著熱忱,準備了很多教材,希望能夠在國立大學傳播學院當中作育英才,遇到學生基礎不好、書讀得不夠多、電影看得不夠多,會覺得恨鐵不成鋼,甚至心灰意冷。
就像我前面說的,老師也是人,老師也會倦怠、也會自私、也會有時候恨不得把學生的頭推去撞牆。
老師可以對教學沒有熱情,可以不愛學生,可是有一個底線千萬不能跨越:老師不可以羞辱學生。

▲ 易智言導演(右)。(資料照/露得清提供)
嫌學生看得書不夠多?不同時代有不同媒介選擇
老師可以怪學生不用功、當學生對學習抱持半吊子的態度,老師當然可以生氣,因為老師如果對教學、對知識是百分之百認真的,他當然希望對方拿出百分之百的鬥志正面對決。
但老師不能罵學生笨(即便這件事情從我們當學生以來就時常耳聞),努不努力是個人選擇、天資與智能狀態卻沒得選。就好像過動兒(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先天身體遺傳,那不是學生笨、不是管不了自己、不是愛惹事生非,那不是選擇。
老師更不能罵學生醜。
這已經涉及歧視,還有人身攻擊,甚至可以是性騷擾。
那些先天遺傳條件,從膚色、外型、身高、體重、智能表現、肢體殘障,精神狀態異常、口語表達障礙,到社會性的家庭型態(單親、隔代教養)、階級、收入、家長職業與社經地位(受刑人、智能障礙、精神疾病)、母語、家鄉......把這些個體無法選擇的弱勢,作為拒絕、責罵、甚至攻擊的理由,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歧視。
學生看的書不夠多、看的電影不夠多,讓人沮喪,我可以同理。但是,本來不同世代,就有不同世代的媒介選擇、文化近便性(例如哈日與韓流的世代差異)、藝術品味,甚至時代精神。
我在政大教了快十年的經驗裡,學生或許沒看過什麼我提過的書或是電影、聽過我放的歌,但是他們也有許多我不知道的文本經驗與媒體習慣,以政大傳院學生的素質,我不認為他們程度很差。
而導演提到學生來修課動機不純,是希望可以在導演作品中露臉,或是希望導演給予創作個別指導。我可以同理,學生不是抱著對知識的渴望,來修課所以感到失望,但這不代表他們欺騙你。
不管是想要露臉、想要攀關係、還是想要個別指導,這不就是他們運用自身可以利用的資源,來尋求機會嗎?他們可以要求,你也可以拒絕。
這是大學,大家都有同等機會,更何況你還是老師,你有社會賦予這個身分的權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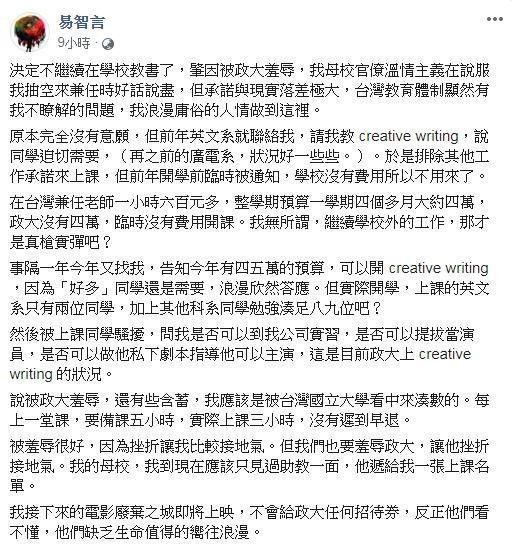
▲ 易智言臉書分享於政大教課狀況,覺得被政大羞辱。(圖/翻攝網路)
教師學生弱弱相殘 制度荒謬失焦
導演或許是出於一種情緒上的沮喪與憤怒,所以連帶地將教學回憶中不舒服的元素,完全混同在一個完整的噩夢情境裡,所以在裡面的學生也面目可憎。
但是冷靜下來,設身處地想想,在整個權力體系之下最底層的學生,怎麼可能會是共犯結構?(某些案例中,或許會出現學生集體霸凌老師,但老師作為一個成年人與社會人,可以向外求助的社會資源網路,仍然大於未成年人。)
你可以不喜歡學生,這是你的權利,沒有人要求老師一定要喜歡學生。但是,不可以對學生人身攻擊,不只是因為學生年紀尚輕、心智不一定完全穩定成熟。
更重要的是,在一個課堂情境裡,老師與學生在權力結構上就是不平等,遑論有些學生會因為這樣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制約,而把老師的話當成真理深信不疑,相信自己又醜又笨,難怪被老師羞辱嫌棄。
這是關於底線的問題。
警察不能侵犯人民隱私、醫生不能對外洩漏病人的病情、機長不能對全機乘客把飛行意外拿來開玩笑、法官不能以私心凌駕公共利益主導判決、藥商不能明知有風險還把藥賣給消費者......。
每種職業都有其不能跨越的倫理防線,這跟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無關、跟職業倦怠無關;而是一個人能不能時常自省、在工作中對得起自己的良知,把自己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是這樣身而為人的基本問題。
而最讓我遺憾的,是事情演變成老師與學生的弱弱相殘,讓制度的荒謬性逐漸失焦,甚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徒增更多傷心不快樂的人。
我現在還是喜歡教書、喜歡當老師,靠存款過活,做喜歡的事。有一天存款會用完、或是我對教書的熱情燃燒殆盡,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會先發生。
我有點無奈生在這樣一個知識貶值、少子化、大學經費緊縮的國家與時代,我也看不到未來在哪裡;但我已經厭倦責怪這一切了,這個問題我也認真判斷過不可能被解決。
只是覺得很遺憾。
一個圈子集合了全台灣最聰明、最有開創性、最有創造力的人們,然後一個愚蠢的制度,就把這些聰明人全部困在一個小框框裡面,互相鬥智廝殺。
那我問你,你要給你教的孩子承諾什麼樣光明的未來?

▲ 李律2012年在大學書院開的第一堂課。(圖/李律提供)
照片是2012年我在大學書院開的第一堂課,全部的人一起躺下來聽學生解說她的創作,我躺在畫面右邊拿著手板。
只有在教書的時候,我可以感覺靈魂的充盈,那是一個純粹的魔法時間,是虛度生命最好的方式。
前天下課的時候,學生跑來告訴我,他在學校裡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個冒充者,好像在扮演一個不是自己的人,只有在我的課的幾小時裡,他不再是冒充者,他是他自己。
這是我開始教課以來最大的禮讚,勝過無數個700塊。
熱門點閱》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李律」個人臉書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歡迎投書《雲論》讓優質好文被更多人看見,請寄editor88@ettoday.net或點此投稿,本網保有文字刪修權。






我們想讓你知道…易智言導演5月10日在臉書怒批遭政大羞辱,兼任助理教授李律指出台灣高等教育的荒謬:大學問題的源頭,在於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制度犧牲教學品質又羞辱兼任教師,老師和學生都是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