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侯
看了一下教育部的資料,2012年度台灣赴日的留學生人數為6千多,僅次於美、澳,居第三位。
這個數字,大致上是呈增加的趨勢,與日本下降的國力幾乎成反比。箇中原因只有等專家來評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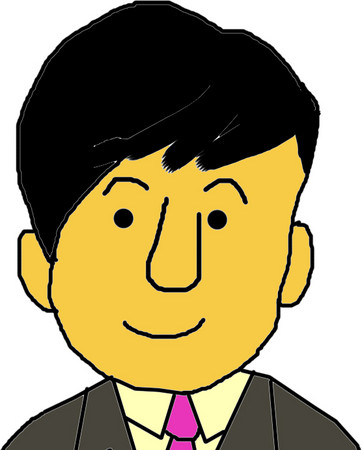 赴日留學的投資,我粗算一下,比美國略少,比澳洲要多。在東京,每月的生活費要5到6萬台幣之間,學費還要另外再算。以一個受薪階級而言,家中出了一個留日的孩子,就勢必要有節衣縮食的心理準備。
赴日留學的投資,我粗算一下,比美國略少,比澳洲要多。在東京,每月的生活費要5到6萬台幣之間,學費還要另外再算。以一個受薪階級而言,家中出了一個留日的孩子,就勢必要有節衣縮食的心理準備。
所以,當年我決定留日,給家裡帶來衝擊不小。母親為之臉色一變,父親為之半天不說話。在他們為我做的規劃裡,我在美國有個姨媽,可以就近照顧我的生活起居,留美絕對比留日來得經濟。父親從一個公家機關的僱員退休,母親肢體殘障,家中經濟狀況連小康都談不上,若非我一路念公立學校,恐怕連拿大學文憑都是癡人說夢。
有看倌說:「老侯,你也真是不懂得秤秤自己的斤兩!你這種狀況,也學人家留學日本,給自己家裡添麻煩?」看倌呀,事出必有因,壞就壞在高中時期認識了一個好友。我和他臭味相投,上下車同樣都有司機接送,他是私家車司機,我是公車司機。此公在台灣,學文不成,學劍又不成,老爸於是資助他到日本留學。成天聽他從日本傳來的消息,無非就是五光十色的新奇體驗,這必然也影響了當年沒見過世面的我。再怎麼說,台灣留英語系國家的多,留日的相對較少,我若英日語皆通,或許可以增加日後自己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事後證實也確是如此)。再加上從小到大,聽父母話已聽成了習慣,在留學一事上,就想「逆反」一下。
留日,就這麼在我心中成了不可撼動的人生目標。
「聽說你要留日,你知道隔壁的劉媽媽怎麼說嗎?她說,日本留學,哪裡是我們這種家庭去得了的。我們那點收入,全拿來供你留日都不夠!」母親坦白地說出了自己的苦惱。
我語帶安慰地說:「媽,大陸的留學生,身無分文也能留日,為何人家行,我不行?我可以打工,工讀賺錢,不會給家裡添負擔。」
媽媽依舊是半信半疑。說實在,連我對於自己能否自食其力都不是太有把握。什麼「辛苦洗盤子、當店員,苦學出頭的大陸留學生」形象,純粹是我向壁虛構而來。誰、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憑著洗盤子刻苦求學有成,這例子我一個也舉不出。但我自認為很有說服力。
媽媽苦著臉,爸爸則仍然是坐在一邊,一語不發。爸爸的一語不發,有另外的原因。家裡有個長輩,當年被日軍打死,爸爸還有個摯友,是個東北人,生下來就因為「九一八事變」成了亡國奴。就連我的外公,也曾在衡陽保衛戰中險些丟了性命,父母週遭充滿了這些對日本理不清的國仇家恨,偏偏我成了矢志留日的孩子(今日看大陸憤青的反日暴動,猶如看到20歲前我的「放大10倍版」)。父母心裡情緒之複雜可想。
我決定在經濟上不給家裡增加太多負擔。只要經濟上能自立,父母不該有太多怨言。我把我稚嫩的規劃告訴父母:「你們預備讓我留美的資金,我只需要一點,就當是『初期投資』,作為學費,去日本語言學校,上三個月的課。之後,我會考公費。我查過了,只要考上了,學費全額補助,每個月還有廿萬日幣的生活津貼,不需要家裡出一毛錢。從開始學日文到考上公費,預計一年。一年後,正式到日本唸書。」
我把計畫說得有模有樣,所謂「初期投資」,其實就是名符其實的sunk cost(沉沒成本),丟到水裡無聲無息。我知道自己正在進行一場豪賭,賭錢,也賭時間。到時只要沒能考上公費,錢沒了,人也不再年輕。
聽完我的話,父親的臉色不太好看。他其實並不在乎錢,為了不讓自己兒子因為家庭因素留不了學,他連抵押房子的心理準備都有了。只是,「留學日本」,畢竟超出他情感容許範圍太遠太遠。
「你要去就去吧,」沉默半晌,父親總算說出他的最終決定。「我們是什麼樣的家庭,能支援你到什麼程度,你自己清楚。到了日本,沒人能照顧你,你要好自為之。」
父親同意放我單飛了,母親不再有意見。這是我長這麼大以來,第一次「脫離父母的手掌心」。就這樣,我赴日留學的計畫正式付諸實施。
學日語,半年之內求得「小成」;準備交流協會公費考試,一年之內取得「大成」。一個廿多歲的年輕人,第一次對自己人生作這樣嚴肅的規劃,如今回頭想想,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彷彿人生最大的雄心壯志,全都在這時迸發。日後的我,竟然是隨波逐流的多、奮勇一搏的少了。
在日本的好友早就幫我張羅好語言學校入學的事情,所以我到東京的第二天,就能直奔語言學校。他建議我:語言學校只上半天課,剩下的時間,與其閑晃,不如打工。一方面賺錢,一方面也算藉機學習真正的生活日語。
「我認識一個台灣人,在新宿打工,就要辭職了,他空出來的缺,你可以遞補看看。」好友這樣遊說我。我覺得他說的不無道理,難得出國,全方面體驗人生,本來也是到海外探險的目的之一。遊學打工,又有什麼不能嚐試呢?
就在我上了一週的日語課後,透過朋友介紹,我和了那位即將辭去打工工作的台灣人初次見面。
「你能來遞補我,我最開心了。畢竟我在店裡打工了半年,和老闆也混得不錯。我一走,老闆還要忙著找人,我覺得怪不好意思的。你來接替我,算是幫了我一個大忙。」那位台灣同鄉說著,表情似是如釋重負。
「你的工作有那麼辛苦嗎?怎麼說得好像很難找到人接替似的?」我不可置信地問道。
「恩,工作內容並不苦,就怕你待不下去。」他詭異地說。
「什麼意思?」
「是賣女人內衣的。店家就在新宿車站下面的商店街。你只需要看陳列架上胸罩、內褲少了,就到倉庫補貨。很輕鬆,時薪980日幣。就怕你身為一個男孩子,在那種都是女客人的地方,待不住。」
「求之不得」,我暗自念著。內衣內褲捧在手裡、甜在心裡,還能領980日幣時薪,人世間有這麼好的事情?這要換成今天,少不得又會被媒體大大渲染成「大學畢業生淪為異國內衣店搬運工」、「血淚:高學歷台灣青年海外每日搬運胸罩內衣」之類,搞得舉國同此一慟。
我表情為難地爽快答應。
第二天,約好下課後,和台灣同鄉會面。他領我到了新宿的地下街女性內衣店,和店長打了招呼。店長是個年約四十的男人,對於我半生不熟的日語,他沒多大意見,只吩咐我要勤快補貨,讓店面陳列架維持好的賣相。台灣同鄉接著交代我作業程序,我一個一個記牢了,當日就交接完畢,走馬上任。
接近三個月的內衣店工讀生活,就這麼展開了。上午上學,下午工作。工作內容確實如那位台灣同鄉描述,「很輕鬆」,除了店長,我是內衣店唯一的男人,和門神一般站在女性內衣店門口不太妥當,我當時的日語能力又不能應付女客人的問話,所以,能做的就只剩搬胸罩內衣。陳列架貨少了,就補貨;倉庫貨少了,就通知店長叫貨。長久下來,別的日語還沒進步,內褲內衣的關聯日語倒是「多識蟲魚鳥獸之名」,進步神速。
三個月下來,我的日語除了內衣店相關用語,其他進步並不明顯,但計劃中的三個月語言學校期限已到,我買了一本「朝日新聞」出版的《天聲人語》社論集作為日語課外教材,收拾好行李回國。
公費考試要求的專業科目(「經濟學」等)水準,與考研究所差不多;日語水準則比一級日語還難(要口試),這些我都計畫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內準備,確實吃力。回國之後,我再在父母的資助下上考研補習班補專業科目;日語則是土法煉鋼,《天聲人語》裡的報紙社論,我選了50篇,每一篇都硬背,一定要背到隨手寫出一字無誤的地步。就這樣七、八個月下來,我已經不怕日文的讀、寫,但聽、說仍是一大問題。補習班的經濟學課程上完了「總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只上了一半。只是時間已無法等我,我硬著頭皮去考。
經濟學,我考得不算太好;日語,我考得不算太壞。信心在五五波上下。值得一提的:日文作文題,竟與我背的《天聲人語》一篇社論若合符節,我下筆如有神,寫出了一篇「社論水準」的日文。結果公佈:我的筆試通過了。但筆試過關,還有口試等著我。外語聽、說能力,哪裡是可以一蹴而成的?我在日本搬了三個月的胸罩內褲,開口能說什麼日語?不安,隨著口試的逼近,逐漸增大,直到口試當天。
口試那天,在台北日本交流協會,四名日籍面試官對著我,輪番出問題。
「侯先生,說說您到日本留學的計畫?」第一名面試官開口問了。
這題簡單,是在我預想範圍內。我鬆了一口氣,答:「我想學習日本的經營管理。」
接著,第二名面試官也開口問了:「喔?日本的經營管理?你認為有什麼好的地方,值得學習的?」
這也是在我的預料範圍。我照本宣科地答:「因為日本的大企業在這地方作得很先進,能掌握市場脈動,作出正確的決定,我希望從中學習。」
夠了,我想。再多的,我也答不出來了。諒你們也不會問得再深入了吧?再深入下去,那就不是口試了,而成了筆試。接下來,只要他們談一些天氣、問一些興趣,這口試也該過關了。我如此樂觀地盤算。
第三名面試官清了清喉嚨,追問:「侯先生,您能不能再具體描述一下,舉例說明,為什麼日本的經營管理,值得你做研究?」
我開始冒冷汗。不就是面試嗎?都說見面三分情,你們怎麼一點都不留情呢?你們聽我結結巴巴的日語也該知道:我就是個賣胸罩內衣的,哪是能回答什麼「經營管理」這類大道理的專家呀!
對了,我是個賣胸罩內衣的!我突然靈機一動,想起了賣內衣時的「SOP」。
「比方說…」
「比方說?」
「比方說,日本店舖管理這方面就做得很好。『陳列棚』上的商品,少到一定程度,就要立刻到『在庫』那裡去『補充』。如果『在庫』仍然不夠,就要『發注』,『受注』的『仕入先』若是不足,就要想辦法『調達』,以免造成『品薄』的印象。在日本,這些都有一套嚴謹的程序,很值得我們台灣學習。」
我一口氣把內衣店所學到的日語全用上了,自信字彙已經超過「日語一級」的水平,就差沒脫口說出「胸罩」、「內褲」。
問我的面試官,臉上展現出滿意的微笑。最後一名面試官,親切地問我打算念哪一所大學,就放了我一馬。一場口試,就這麼完成了。
最終結果發表:我順利考上了交流協會公費。一切符合了我在一年多前規劃的藍圖,母親為此喜出望外,當初聽說我決定留日時的不安陰霾,一掃而空。
我興奮地對母親說:「留學,可以不用花錢的。這你沒想到過吧?」我說著,突然注意到桌上有個不曾見過的牛皮紙袋。
「這是什麼?」我問道。
母親說道:「房屋產權證明。你爸爸早就準備好了。他說,要是你沒考上公費,就拿這個去辦抵押貸款,說什麼也要供你留日。」
我看著仍是沉默的父親,不知怎地,感覺自己眼眶有些濕潤。
後記:「時薪980日幣」的內衣店工作,換算起來,甚至高出我回國後人生第一份正職(月薪3萬6千)。3萬6千台幣,當年已經不算高薪,為此大喊「公司對待留學碩士太刻薄」的同事大有人在,甚至因此憤而離職。誰知道十多年下來,台灣連這樣的薪資水平也岌岌可危。而東京時薪一千日圓上下的工作,至今仍是到處都有。這十多年下來,兩地的薪資水平都交了白卷呀。
編按:作者老侯妙筆笑談過往,卻心繫台灣未來,原本題目為「留日留日,日本是你留得了的?--希望能給年輕人一點正面激勵的作用」,因機制關係,無法完整呈現,僅此說明;亦盼有為青年能接踵壯遊,或奮起向上,為人生添加色彩。
●作者老侯,碩畢,在日本謀生的台灣上班族。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