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侯
前一陣子,日本一家商店發現一張偽鈔,報警偵辦。
說「偽鈔」,其實不精確。騙徒刻意拿了一張琉球才見得到的冥紙,模樣像極了日幣的萬圓紙鈔,魚目混珠地騙過了店老闆。
為了說明冥紙是個甚麼東西,日本的新聞節目還特地請專家解說,把這個日本本島不熟悉的風俗,介紹給觀眾。這也間接說明了:在祭拜亡者的習慣上,琉球風俗近似漢文化,卻與日本迥異。在日本,偶爾路過事故現場,親屬最多放置一瓶鮮花悼念死者,沒有我們又是道士作法、又是冥紙滿天那樣的熱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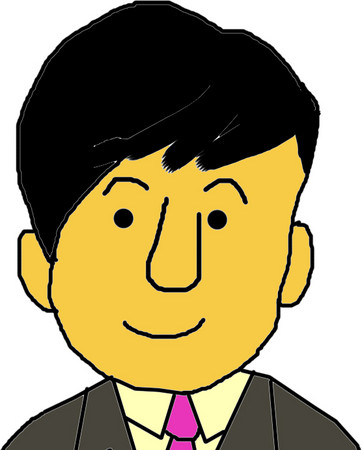 那麼,是否我們比較迷信,日本人比較不迷信?當然不是。我們的神棍,最多把信徒的錢騙到手,或者把女信者騙上床。日本所謂的「新興宗教」,騙財騙色已經是雕蟲小技,奧姆真理教那般大規模殺人,這就遠非我們台灣神棍能比的了。
那麼,是否我們比較迷信,日本人比較不迷信?當然不是。我們的神棍,最多把信徒的錢騙到手,或者把女信者騙上床。日本所謂的「新興宗教」,騙財騙色已經是雕蟲小技,奧姆真理教那般大規模殺人,這就遠非我們台灣神棍能比的了。
那次,和同事一起聚餐,茶餘飯後的話題,不知怎地談到了宗教。我沒信教,只是應酬兼應景地談一談我的看法。大家瞪大眼睛,聽得入神。
我沒什麼高見,純粹把在台灣的所見所聞講了一下,述而不作。極稀鬆平常的見解,但大多數在場的日本人同事都沒聽過,所以聽得津津有味。
「為何日文裡的慶典,要叫做『祭』?」我開口問道。
大家面面相覷,沒人答腔。
我接著說:「『祭』,寫成漢字,是供桌上,一隻手,捧著一塊肉,意思是祭神。聚會、慶典,是人的歡宴,和神有什麼關係?連校慶也叫做『校園祭』,這好不好笑?校園是神創造的?」
話說完了,大家聽著,紛紛點頭。日本人點頭,多半是表示聽進去,不一定表示贊同。
一個同事說:「嗯...聽你這麼說,確實是有點道理。」
「可是,神是無所不在的,所以叫做『祭』,這也說得通吧!」一個同事接著說。大家聽了,不覺莞爾,笑成了一片。
那時,我依稀感覺到一個女同事,雪江,坐在一邊,不搭腔,只是默默地聽著,與週遭的氣氛不太搭調。
飯後,大家各自付帳回家。雪江選擇了一個四下無人的時機,突然叫住了我。
「侯桑,我可以和你談談嘛?」
我略為一怔,詫異地問她:「怎麼了?」
「可以耽誤你一點時間嗎?到附近咖啡廳坐坐聊聊?」
「嗯,好呀。明天週六,待晚一點沒關係。」我爽快地答應了,但從雪江認真的表情,我預想這不會是一個輕鬆的「聊聊」。
我們到了東京「日本橋」附近的一家咖啡廳。各自點好了飲料,拿到座位上,坐好。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要告訴我呀?」我坐好後開門見山地問。
雪江說:「侯桑,你知道『真言宗』嗎?」
「恩...聽過名字,是佛教的一個宗派吧?僅止於此。其他不知道。」
「我最近,被『真言宗』的一個大師相中,要我作他的嫡傳弟子。」她嚴肅地說。
「嗯?那...很好呀!妳有這個慧根嘛!」
「你不知道的,我很苦惱。我其實從小就有一種能力,會看到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我聽著,身上隱約起了雞皮疙瘩。
「我甚至經過不認識的人家,還能感受到那戶人家是否會出事。小時候有幾次,和爸爸一起散步,路過鄰居家,我脫口說出『這戶人家會死人』,第二天果然靈驗。爸爸知道了,要我以後什麼都不要說。」
雪江喝了口咖啡,繼續說:「我不想要有這種能力,但沒辦法,那些東西總會找上我。我閒暇時,只想待在家裡(神奈川縣),不想來東京。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搖搖頭。
「東京以前發生過大空襲。你知道嗎,我路過隅田川(東京台東區的一條河),還可以看到一堆河川上的浮屍。」
我當時半信半疑地聽著。如果這都是真的,這女同事未免太可憐了。
「銀座,日比谷公園,我也不想去。有幾次路過,突然就有全身燒焦的人跑出來,抓住我的手,要我給他們一口水....。」
天哪,東京大空襲,至今都過了一甲子了。真有這些怨靈,陰魂不散地盤距在原地那麼久嗎?
這實在是我無法理解的世界。我只能靜靜地聽雪江說,什麼話也插不上。我事後查過「東京大空襲」,銀座、日比谷公園,確實都是重災區。隅田川沿岸則是遭到美軍燒夷彈轟炸,身上著火的居民不論會不會游泳,紛紛往河裡跳,其結果就是河面滿是浮屍。
這完全與雪江描述的慘狀相符合。
接著,雪江就開始說她和真言宗那位大師的奇遇。
雪江說,她自己也多少會看人相貌。有些人的相貌就是「不對」,看了就是不喜歡,這和醜與美無關,就是磁場不對。
「我長期被這些事物困擾。有一次,我因為生病住院。住院期間,有一天,在醫院的會客室,見到一個相貌堂堂的人。下意識在想:我要是不跟這個人說幾句話,這輩子會後悔。於是我主動和他說...。」
「妳主動對一個不認識的人開口了?」我驚訝地問道。眼前的雪江,給我的印象一直是美麗而文靜的,不像是會主動搭訕的人。她會開口和陌生人說話,想必是有什麼驅使著她。
「他是怎樣的人?」我問道。
「那個人自我介紹,說是真言密教第159代大師。這是從平安時代(9世紀到第13世紀的日本)一路傳來的。精確地說,是『真言密教天意真觀流天意真觀派』。」
這一大串教派名字,我是在她用手親筆寫下之後,才知道她說什麼。
雪江繼續說:「他一見到我,就斷定我與他有緣,要收我做弟子,他連法號都為我想好了。」
「法號?」我稍微驚訝了一下。這情節,像極了任何一個病急亂投醫的人,遇到一個見獵心喜的術士。
「恩,叫做『月光』」雪江說。
雪江她繼續描述著那位密教大師的種種神蹟。這位大師能看穿一個人有無被「依附(附身)」,能從面相斷人善惡,能知人的大限....。這位大師當下把雪江心中煩惱的問題,一一言中,讓雪江佩服不已。
我聽到此,也開始對這位大師感到好奇。或許雪江真的「適逢其人」,只是我不清楚罷了。也就是從這次深談之後,雪江把我視為公司內唯一可傾訴煩惱的對象。所謂「唯一」,是有原因的。雪江曾在父母陪同下,看過精神科。精神科醫生針對她的「症狀」給了一個高深的醫學名詞,高深到我在她轉述過就忘了。吃了鎮定劑之類的藥物,依舊無濟於事。鎮定劑管得了上半夜,管不了下半夜。下半夜,她醒來了,多半是被耳邊的「人」吵醒。
雪江和父母住在一起。自從被診斷為「精神有問題」以來,她不敢和任何人再提她所見到的異像。在日本,若是公然談起這些事情,很可能會被公司察覺她的精神狀況異常,以不適任為由辭退她。到時她連生活都成問題,只能以一個精神病患的名義領殘障津貼。所以,那晚她願意和我透露這些事,實在是長久下來累積的結果,她需要一個宣洩的管道。
她的父母則是限制她平日的花費,每月薪水必須交給媽媽保管,每天只能拿兩千日圓零用,就是怕她「心智不正常,被人騙」。
我同情她的遭遇。雪江畢業自「立教大學」,她自嘲地說,立教非一流,非三流,是一點五流。但是從她平日的聊天,我知道她絕非「心智不正常」,她父母應該清楚。
但是,她不時遇到的異像,則始終困擾著她。有一天晚上,她發簡訊過來。
「出現了」
「什麼?」我回覆。
「又像以往一樣,出現了。一個小孩,在我床前又跳又鬧!」
我看著手機裡的簡訊,不禁打了個寒顫。她接著又發來了一個簡訊:「應該是『座敷童』!是會給人們帶來幸福的。我應該不用操心」
我不知道什麼是「座敷童」,上網查了一下,才知道這是日本民間流傳的一種小精靈,專門搗蛋,但通常不會惹事。
我有些不太高興了。雪江或許真的看到異像,但我不相信有什麼「座敷童」。如果「座敷童」可信,三太子又何嘗不可信?孫悟空和豬八戒又何嘗不可信?但這些都只是民間故事。所有的民間故事角色統統都成精成怪,這世間精怪何其多,還有完沒完?
我開始懷疑雪江。她的鬼故事可能有真有假。她是否在利用我的同情編故事,只希望多博取一點關心?
我的不滿,在和那位「真言密教大師」過招後,到達最頂峰。
雪江沒有正式答應成為那位「大師」的弟子,但過從甚密,儼然已是他的入門弟子。雪江自心底把「大師」奉為高人,言聽計從。和我熟稔以後,她提議把我的照片拿給那位「大師」驗一下。據說,好人壞人,「大師」一驗即知。
我也很想知道這位「大師」的神通,所以,答應了雪江。
某天,她和「大師」聚餐,順便讓「大師」看看我的照片。我在公司加班,一邊等著對方「檢驗」後的結果。
晚上8點多鐘,雪江發來訊息:「給大師看了你的照片」
「如何?」我回覆。
「他說:你是一個30歲、略顯疲憊的上班族。準吧!」
我愣住了。接著回覆她:「是嗎?還說什麼?」
「說你適合作上班族,別出來做生意什麼的。」
我沒再追問了。我年紀「何止30」!雪江是清楚的。「大師」猜我是30歲,只因為我照片顯得年輕罷了。和實際年齡差了不只一截,以一個「大師上人」而言,這是無法以誤差值來搪塞的。至於「疲憊」這類不著邊際的形容詞,則可以用來泛指任何人。
所謂「大師」,技止此耳!
但雪江明顯信之不疑。
雪江又發來了:「他說,從照片看來,你被一個30多歲的女鬼纏著。」
我把手機蓋上,再也不看了。連活人都認不清的「大師」,能認得清死鬼?
隔天,我們在公司見了面。我邀雪江到會議室,把我的疑惑統統和她說清楚。
「雪江,我相信妳能看到那些東西。但妳找錯人了。那個大師只是個神棍!」我憤憤地說。
雪江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說:「為什麼?」
「把我猜成30歲,這不是誤差。這樣的大師妳也信?」
「但是他說你是『很累的上班族』,沒說錯呀!他還說,你身邊跟著一個女鬼,只有我救得了你。」
我發現我根本無法生氣。單方面生氣無法解決問題。雪江很可憐,她是真的需要「大師」,不論是從科學的角度或民俗信仰的角度。這個「真言密教大師」就是利用了雪江這一點,趁虛而入。
我後來忙於客戶專案,和雪江也沒再連絡。幾個月後,公司同事傳來消息,說雪江離職了。雪江是和「大師」雲遊去了?還是好好療病了?再不得而知。
倒是我還有個疑問,一直未解:那位「一直跟著我的30多歲女士」,是何長相,「大師」怎麼就不肯透露呢?我愛美魔女,大家都知道的呀!
●作者老侯,碩畢,在日本謀生的台灣上班族。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