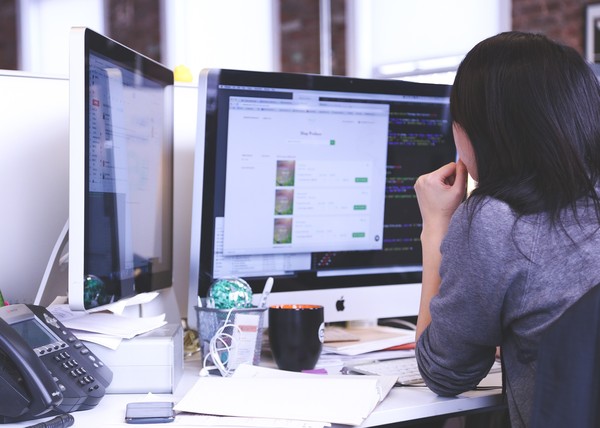
▲台灣的勞基法,要求所有的公司都把員工當成工廠的作業員看待,按時計酬。(圖/pixabay)
●林宜敬/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畢業,美國布朗大學電腦科學博士。2002 年創辦艾爾科技公司,推出專業的聽力及口說訓練軟體 MyET,現擔任執行長。
過去六個月裡,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在重寫改善我們公司的一個核心程式。但就在上個禮拜,我卻發覺我新寫的程式有一個 “Memory Leak” 的問題,也就是說,我的程式執行的越久,使用的記憶體越大,效能越差,甚至還可能會當機。而我花了許多的時間,卻一直找不出問題在哪裡。
恰逢星期六,又是颱風天。但是我仍然放心不下那個程式,所以下午又一個人跑到辦公室裡去找問題。我一邊上臉書,一邊聽滾石合唱團跟披頭四的音樂,一邊寫程式做實驗。而當我的思緒被卡住的時候,就跑去整理公司的兩個水族箱。
但我仍然找不到那個問題。一直等到 George Harrison 開始唱 "My Sweet Lord" (我親愛的上帝)的時候,我終於領悟到,應該是上帝要我休息了。所以我就將有問題的程式列印出來,鎖上公司的大門回家了。
臨睡前,我躺在床上,又把那段列印出來的程式拿出來看,結果居然很快的就找到問題。而今天一早我跑到公司裡,把那一行有問題的程式修改掉,果然很順利的就把那個 “Memory Leak" 的惱人問題排除掉了。我非常的興奮,興奮到在空曠的辦公室裡大吼。
我所說的狀況,不過是一個軟體工程師的日常。但是在許多台灣政界人士跟鄉民的眼裡,我是一個被公司壓榨的工程師。
我在颱風天上班,我在週末上班,我把我的工作帶回家做,我沒有計算公時,也沒有打卡。不過,倒是沒有人會要我去舉報我的老闆,因為我就是老闆。而現在在台灣,只有老闆才能自行決定上班的時間。
台灣的政治人物總是說,台灣的產業要升級、要轉型、要發揮創意、要做高價值的軟體產業。但是在政策上卻反其道而行,一部勞基法,要求所有的公司都把員工當成工廠的作業員看待,按時計酬。
像軟體這種靠腦力的產業,每個員工的能力差距很大,工作的習慣也很不一樣。一個每天工作12小時的程式設計師,產出未必比一個每天工作6個小時的程式設計師大,所設計出來的程式也不見得比較好。
反之亦然。
有些程式設計師喜歡在公司裡專心工作,做完就下班,因此他們上班的時數不多;有些工程師喜歡一邊工作一邊玩,並藉此激發出自己的創意,因此他們上班的時數多,產出也多;但是也有一些工程師一邊工作一邊玩,卻從來都沒有什麼創意,因此他們上班的時數多,產出卻沒有比較多。
也就是說,計算員工的工時,對一家靠腦力與創意來賺錢的公司來說,根本是沒有意義的。
一個工作環境友善而重視創意的公司,並不會去管員工在公司在公司裡做什麼。員工寫程式也好、上網也好、靜坐冥想也好、聊天喝咖啡也好、玩樂器唱歌也好,只要一個員工能發揮創意,做出好的產品,就是好員工。
而如果員工的思緒被卡住了,想去公園裡走走,或是去打場球,或是去大賣場裡逛逛,或甚至回家去帶小孩,只要去跟上司講一聲,公司既不會干涉,也不會扣薪水。因為公司在乎的並不是員工在辦公室裡待了多少時間,而是員工是否能做出好的產品。
而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矽谷的科技公司大多是責任制,而不是按時計酬。
通常從事知識產業的公司會分紅給員工,也會分股票給員工,但就是不會發加班費給員工。所以在矽谷高科技公司裡工作的員工,通常是靠著分股票或是分紅而賺大錢的。
我到現在還沒有聽說過,有什麼人在矽谷是靠著領加班費而發大財的。
其實在二十年前,台灣也有很多的「電子新貴」,他們同樣是靠著分紅與分股票而賺了很多錢,而不是靠著領加班費發大財的。
偏偏後來台灣修改法令,把員工分紅費用化,讓新創公司分股票給員工的意願大減。結果就是一個公司跟員工雙輸的局面。
我所知道的美國矽谷,以及二十年前的台灣電子資訊業,新創公司裡的老闆跟員工並不是涇渭分明,更不是對立的。
新創團隊裡的成員要不是公司的股東,就是可以參與分紅配股。大家的向心力都很強,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就是某種程度的老闆。
而現在的台灣,在政客與酸民的煽風點火之下,老闆跟員工是涇渭分明,甚至是對立的。只有公司的老闆可以正大光明的讓自己採用責任制,對自己的工作時間與產出負責。
矽谷的新創公司講究的是整個團隊的創新能力,而台灣的公司只能靠老闆自己發揮戰力。也難怪,台灣的新創公司成功的不多,倒是個人工作室越來越多了。所以每次跟台灣政界的朋友談新創產業政策,我就一肚子火。
台灣一直喊著要產業升級、要轉型、要發揮創意、要做高價值的軟體產業。但是卻要求軟體公司把員工當成生產線的作業員來管。
這真是一個精神分裂的創新產業政策。
熱門文章》
►提高基本工資,台灣會不會出現「邊際勞工」?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臉書。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雲論》提供公民發聲平台,歡迎能人志士、各方好手投稿,請點此投稿。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