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侯
最近,我的台灣朋友們到日本來看我,來了一團又一團,我當自己人緣好,正在美得冒泡時,只聽大家眾口一聲地說:日幣貶,看你和到木柵看猩猩都差不多便宜,當然不來白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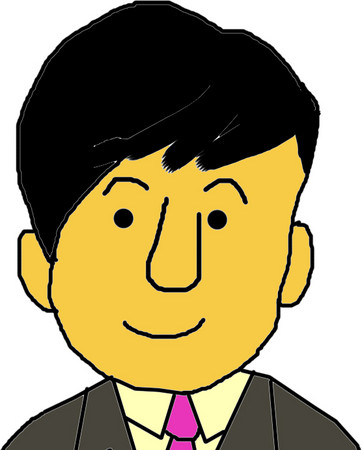 日本近,再加上日圓貶,台灣來日的觀光人潮擋也擋不住。前一陣子,馬總統向日方代表抱怨,說台灣對日本的觀光產業處於大幅逆差狀態,要日本檢討,且連抱怨了兩回。依我看,這不是日本單方面檢討就能改善的,「貶日圓、救經濟」,本來就在日本內閣計畫中,你們的鈔票跑到人家的口袋裡,人家只會越「檢討」越得意。
日本近,再加上日圓貶,台灣來日的觀光人潮擋也擋不住。前一陣子,馬總統向日方代表抱怨,說台灣對日本的觀光產業處於大幅逆差狀態,要日本檢討,且連抱怨了兩回。依我看,這不是日本單方面檢討就能改善的,「貶日圓、救經濟」,本來就在日本內閣計畫中,你們的鈔票跑到人家的口袋裡,人家只會越「檢討」越得意。
既然大家都愛來日本、特別是來東京玩,我忍不住建議各位看倌:您若是闔家前來,可別因為初來乍到,按捺不住興奮情緒,一早就趕搭電車到處閒晃。如果是碰到通勤高峰時間,一個弄不好,就會搞得妻離子散、身首異處。
甚麼叫做「妻離子散」?您闔家搭車,和一群上班族擠在車廂裡,您的夫人被擠到天之涯,您的一雙兒女被擠到海之角,您又自顧不暇,擠在門口進退兩難,如此,不到目的地,全家再難團圓,這就叫「妻離子散」。
甚麼又叫做「身首異處」?您不過是想伸個脖子查看車廂內的路線圖,被一群突然湧進車廂的OL擠得動彈不得,稍一挪動身子,瓜田李下,被人一口咬定您吃她豆腐,語言不通下,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如此,除了維持歪脖子的扭曲姿態以自保,別無方法。這就叫「身首異處」。
這是有名的東京「通勤地獄」。東京上班族也早就練就一身「我入地獄,你們誰也別攔」的本事。望著早就擠得水泄不通的車廂,換成凡人,多半會打消搭車念頭,但東京上班族早就超凡入聖。車廂內密不透風的人牆,對他們而言,不是人牆,是人肉墊,擠出個凹窟窿還是能鑽。我就親眼見到一個西裝筆挺在月台等車的上班族,車廂內分明毫無空間,他連想都不想,一轉身,屁股朝著人牆猛頂,硬是頂出一個差可容人的空間後上車。
總之,除非您太想體驗東京上班族地獄般的通勤光景,我奉勸各位看倌,除非必要,別在通勤時間湊這個熱鬧。看著「滿員電車」,遠觀可也、訕笑可也、照相可也,這一照,說不定我還入了您的鏡頭。因為這就是我在東京做上班族的每日實態。
日本上班族予人勤勉的工作形象,有趣的是:根據日本「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所發表的最新《國際勞動比較》,日本人一個月平均工作時數為147.1,換算成每天的工作時數,則是七個小時半不到,比韓國台灣還低。都說日本上班族辛苦,卻全在數字上蒸發掉了。苦到哪去,只有天知道;至於為何而苦,則是連我這個日本上班族都不知道了。有一次,因事和台灣中國信託的銀行小姐通越洋電話,銀行小姐知道我在日本工作,興奮地說:「侯先生,您在日本上班喔?」
「是的。」我回答。
「好好喔!我好想在日本上班生活!」
銀行小姐語調異常高亢,不太像是客服小姐的應酬話。但從年輕女孩亢奮的語調聽來,我「在日本工作過日子」這一點,看來就剩下「騙美眉」的價值了。
就這樣,幾番思考後,我在日本辭去了工作,開展人生的新頁。
沒了上班族身分,本該是海闊天空,沒想到這在日本就是意味著墬入另一個階級。這是真正始料未及的。厚生年金沒了,房子租不了、房貸借不了、銀行戶頭開不了、信用卡辦不了。從前留學時,一個大陸同學半開玩笑地說:「中國算甚麼社會主義國家?日本才是!」話雖戲謔,但玩味起來確有幾分真理。日本的「會社(公司)」,與大陸當年的「人民公社」差可比擬。台灣的全民健保,是由政府主導辦理;日本上班族的健康保險,則是由「會社」所屬的產業公會自負盈虧。日本大的「會社」照料員工生活,無微不至,和當年大陸「人民公社」包辦人民生老病死一模一樣。這就是為何日本人進了「大手企業」(大公司),就如同太監淨了身一樣,再轉型都難了。
「會社」讓員工每月拿同樣的錢,做著一樣的事,是因為「會社」幫著員工擋住了外界的經營風險,作為回報,員工自然是任勞任怨拿死薪水。我離開「會社」,就意味著我從此脫離這個井然有序的群體組織,自己承擔風險。這一點天經地義的道理,我是在獨立營業後才真正感悟。
海外仍有一片天
我離職後,一度考慮重回台灣人力市場,投石問路之下,發現台灣業者對於開拓跨國系統市場大多興趣不大(唉,人各有志),我努力培養出來的跨國經驗,看得上眼的台灣企業不多,繞了一大圈,發覺還是留在日本機會多些。閑散幾個禮拜後,有一天,接到一通電話。是一家印度系統公司在日本的負責人打來的,自我介紹名叫「莫圖」,是個印度人,但日語極其流利,看來也是在日本待久了。
「侯桑,聽說你在日本,都是負責做跨國企管系統的?」
「是的。慚愧,也只會這個。」
「呵呵,我是透過你的日本朋友介紹的。說你腦子好,溝通能力強,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和我們合作?我們有個大案子。」
莫圖提的日本朋友,我大概猜到是誰。當初我和這個日本朋友意氣風發決定要「一起開拓市場」,但他最終臨陣脫逃,還是回頭做上班族了。大概是基於內疚,把這送上門的機會讓給了我。
「我很樂意試試看。請問是甚麼樣的案子?」我問道。
「是一家歐洲的機械製造商,要在他們的日本分公司導入系統。我們正在和別的系統商競標。這案子金額不小,我們務必想拿下,可惜的是,我們在日本找不到合適的雙語系統人才。」莫圖解釋道。
莫圖說,不少日本人聽到這案子內容「要和老外打交道」,已經先懼了三分,再加上不景氣,敢於出來闖的人越來越少,大多數選擇在一家公司的資訊部門安穩窩著。所以找個合適的人才實在不容易。
完全符合我所料。日本年輕人逐漸「內向」,這幾年特別明顯。以絕對數來看,2011年出國觀光的日本人,共一千六百多萬。看官們要是覺得在海外見到日本人的機率不低,原因很簡單,因為日本一年就是送了這麼多人出去。但以人口比例來看的話,日本人出國的比例就不高了,在亞洲各國中,甚至還低於台灣、香港,僅僅14.6%(台灣為40.4%)。到了20多歲還沒出過國的日本人,越來越多。
我認識一個日本人,想到出國就頭疼。問他頭疼甚麼,他回答「出了國就不會點菜」。
細想一下:看著滿紙外文的菜單,不會點菜,確實是個傷腦筋的事情,但不至於要人命。「點菜」可視為難關之一,但絕對是最後才想要克服的「難關」。對於我這種天生樂觀的人而言,甚至還視為「樂趣」。
日本是個各方面都便利的國家,便利到任何一個日本人、到了任何一個海外國度,都會大感吃不消,想早早回國。便利店到處有、自動販賣機到處有、各種服務到家、連上個廁所都有自動洗屁股機...,日本越是便利,離開日本就活不下去的日本人,也就越來越多。我以前在東莞郊外做過的日資工廠專案,甚至看到日本人把洗屁股機都帶來這個窮鄉僻壤了。
所以,「點菜」問題,僅是壓死日本人的第一根稻草,怕沒便利店、怕沒自動販賣機、怕生病、怕沒法洗屁股...都是稻草,全壓上來,成了稻草堆,有幾個日本人受得了?
但,這不正是讓我這種有志於「做跨國生意」的人,有了做生意的機會?連外國長啥樣子都沒見過、想到外國就怕的日本人那麼多,這生意我們不賺,誰賺?
為了測試我的英語能力,莫圖改用英語口試,我過了關。幾天之後,莫圖再請人測試我的專業能力,我也幸運通過測試。如此這般,莫圖認定我合格了,兩人於是約在他的公司見面。
莫圖本人身材高大,膚色黝黑,在印度人當中,也算是深色人種。我後來才知道,他出身的「比哈爾邦」,是印度種姓制度中「賤民」人口極多的地方,他卻憑著自己的努力,在海外闖出一片天。知道他的身世與經歷後,真覺得自己十幾年上班族的日子過得太安穩。
莫圖和我親切握手,簡短寒暄過後,隨即進入正題,談如何一起拿下他口中的這個「大案子」。
「這家歐洲機械公司,為了替在日本的分公司導入系統,系統專案負責人早就與幾家日本當地的顧問公司接洽過。我們是透過好幾層關係,才和這家公司搭上線。他們總算願意給我們一次機會,讓我們參與競標。」莫圖道。
「這麼說來,我們算是中間殺進來的?」我問道。
「沒錯。說起來,我們起步比別的公司晚。」莫圖邊說,邊把資料攤開,和我解釋了一下這家歐洲公司的系統專案內容。
「他們在東京有公司,在靜岡有工廠。這次的系統導入,除了日本,還包含中國上海。侯桑,你是台灣人,你的中文…?」
「中文沒問題。」
「知道中國當地的會計制度?」
「知道,我在中國做過專案。」
莫圖滿意地點點頭。只是這事不是他滿意就能拍板定案,最終還得客戶說了算。但是我有信心:取悅日本人上司同事,我自忖能力不足(早放棄了);取悅日本或老外客戶,我自視游刃有餘。
所謂「內戰外行,外戰內行」也。
於是我與莫圖簽了約。我帶領他的印度人團隊,衝鋒陷陣打這一仗。我不會再回日本公司,我也回不去台灣公司,繞了一大圈,我又到了「外商」。這次是印度商。
你不知道的印度人
我帶領的團隊共四個印度人,一個銷售系統專家,一個庫存管理系統專家,兩個開發人員,全都是資訊領域的練家子。
印度人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四肢簡單,頭腦發達。
他們四肢簡單到了甚麼程度?印度自1952年以來,56年當中,就不曾在奧運比賽中拿過一面以上的獎牌。以人口來平均,印度的獎牌數一直都是敬陪末座。2006年亞洲盃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女子800米田徑銀牌選手,後來「女選手」被揭發居然是個男的。「派個男的參加女子賽,也只能跑出個第二」,笑掉人的大牙。
但也正是這麼一個體育弱國,卻傾全國之力發展IT頭腦。光是2012年一年當中,印度的IT外包產業就佔了全世界市場的58%,金額高達1000億美元以上,比中華民國去年歲出總預算還高。投身IT產業,是印度種姓制度下「賤民」的晉身機會。我的印度朋友們,自莫圖以降,全都是藉此嶄露頭角。他們做IT,有著翻身的強烈慾望,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
但在日本的他們,有個致命傷:日語再精通,卻多半不懂漢字。所以,與日本籍客戶溝通,特別是書面溝通時,就得仰賴我了。
而我僅有一個禮拜多的準備時間。一個多禮拜後,就要到客戶所在做「提案」。我熟讀了客戶的資料,和我的印度團隊分析了客戶的可能需求,沙盤推演了多次,也漸漸和這幾個印度弟兄混熟。
與印度工程師們打交道有幾個小難關要克服。印度人儘管大多能說英語,但說出來的英語是出了名的難懂,說得又快,幾乎每個字要吐出來之前,總得在口中來回反彈多次,這才好不容易迸出;迸出來的字,又像上了彈簧一般,回音不斷、繞樑不絕。再來,就是印度人針對「Yes/No」的反應自成一系,表達Yes時,腦袋不是點頭,而是如同鐘擺般左右擺動。由於「Yes/No」的腦袋擺幅差異不大,常常讓人摸不清頭腦。
印度人的飲食習慣又各自不同。有的只吃雞肉,有的只吃蔬菜,大多不吃牛肉。上個餐廳,得把菜色內容過問再三,才敢動手吃。這裡說的動手,有時是真「動手」。我的印度同事,一隻手就能把餅撕開,一口一口地塞進口裡,絕不假手餐具。看得雙手拿刀叉的西洋人、或單手用筷子的東洋人,都要自嘆弗如。
這場仗的勝敗,關係到大家的溫飽。我的小組裡,一個叫「瓦拉」的印度同事,希望賺一筆錢後回家討媳婦;另一個「山繆爾」,則希望靠著在日本賺來的錢給家裡添一部摩托車。沒人能等閒視之。
瓦拉說,這案子拿下來的話,他就先請三個禮拜假,回國迎娶新娘,風風光光辦一場婚宴。
「侯桑,你有把握否 (Hou san, are you really confident) ?」瓦拉問起。
我琢磨了一下,道:「瓦拉,告訴我,你老婆到時還等你不等你?」
「當然!」瓦拉自信滿滿地回覆。
「你只要把老婆顧好,我就有把握!」
說完,大家大笑。我也笑,只是笑得不踏實。「We are the best」,真假不說,但氣氛得由我來營造。還好,印度人大多比日本人樂天。印度人邊幹活邊自哼自唱;日本人邊幹活邊自言自語。面對這樣的印度同事,我只需一點點激勵的話,大家便士氣高昂。
不眠不休把展示資料準備了四天,做出一份「提案書」簡報。莫圖過目,表示滿意。我心裡不禁大嘆:「日人印人,何相異乃爾!」簡報內容有時反映了作者的思維與個性,好壞與否,是個很主觀的東西,但在日本公司,個人主觀是無法突出的,一份「提案書」被上司改得面目全非,已屬常態;如今和印度人第一次合作,印度夥伴即對我用之不疑,我深感「得君行道」之餘,自然亟思以行動報答了。
由於客戶的系統不僅要導入日本,同時還要導入中國。在東京提企劃案當天,客戶歐洲總部請來了中日兩地的業務負責人一起參加,聽取我們系統商的企劃案。同樣參加的,還有另一家競爭廠商,OO公司。
OO公司兵強馬壯,在亞洲早就是獨霸一方的顧問公司,我聽到對手名字,老實說,心涼了一半。而客戶採取的,又是一翻兩瞪眼的做法:由客戶方面提問,兩家廠商作答。會、不會,無法以吹牛皮帶過,只能用真功夫。這是我在日本商場的第一場仗,萬萬沒想到是這樣一場硬仗。
知道是硬仗,只有硬著頭皮打。我們戰戰兢兢迎來了到客戶處提案的那一天。
短兵相接
客戶的東京分公司,位在東京「千代田區」兩個地下鐵車站之間,從哪個車站過去都差不多距離,用日文說,就叫做「中途半端」,意味著從哪個車站過去都得走一段路。我為了怕大熱天裡大家走得心浮氣躁,出了車站便叫了計程車,一行人搭車直奔客戶辦公樓所在。
我們表明身分來意後,客戶櫃台小姐對我們鞠個躬,隨即領我們進了會議室。我們明明是準時到達,但客戶會議室裡的大圓桌就幾乎坐滿了人,「會無好會」的氣氛,從一開始就明顯感受。會議桌上,歐洲面孔五、六人,坐於左側;亞洲面孔十多人,坐於右側。有幾個亞洲人,穿得特別西裝筆挺,想必是對手OO公司的人馬。
我們幾個人坐定,從包裡掏出電腦,放在會議桌上。會議主持人隨即宣布會議開始。主持人來自瑞士,是負責這次亞洲區系統導入的專案經理,出席用戶則來自日、中等國家。所以會議主要以英語進行,但用戶的英語說得有些吃力,日本分社的社長索性連英語都不會,看來雖然是歐洲公司,海外分公司和總公司之間,聯絡並不那麼緊密。
會議議程共進行兩天。主持人先把上午議程介紹完後,就正式開始會議。對手OO公司先上台做簡報,打扮體面的男顧問以日語主講,梳妝整齊的女翻譯作英語即席口譯。男的一句,女的一句,簡報內容做得中規中矩,不虧是饒富經驗的團隊。只是會議室內昏暗燈光所引起的催眠作用,不消廿分鐘,出席者多人開始夢周公。我見狀,暗自叫苦:現在尚且熬不住,等一下輪到我,豈不全體趴在桌上睡,到時誰還看我們辛苦準備的內容?
「接下來,請XX公司的侯先生為我們解說。」
輪我了。台下幾個出席者揉揉眼睛,強打起精神。看著他們的模樣,我想,等一下開講,大家重夢周公,恐怕只是時間的問題。我臨時想出了一個台詞。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紹。想必大家看我的臉,都猜出七分了:我是台灣人。」這話分別以英、日語說出,說完隨即暫停。
台下先是鴉雀無聲。幾秒的沉默過後,一個意識到這是個笑話的歐洲人,首先大聲笑道:「Sorry, I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對不起,我不知道哪裏不一樣)」話一出,全場跟著笑成一片。幾個本來昏昏欲睡的出席者,似乎也跟著精神一振,笑出了聲。就連對手公司的幾個人,也忍不住掩著嘴笑。
我安心了。睡魔趕走之後,接下來只要照著事先準備好的簡報,行雲流水地說完即可。為了讓與會者多所參與,我加了一些互動問題,讓各國用戶「各言爾志」,只是老中說英語,「six」發音像「sex」;老日說英語,「fax」發音像「fuc#」。各自陳述對系統的需求時,老日說:「We want to fuc# our customers」,老中說:「We have sex offices」,用戶們語音才落,遠遠見到我的印度同事個個如鐘擺般搖頭。如此這般,一場多國口音夾雜的的會議,開得活色生香,大家從頭到尾忍俊不禁。但是很明顯,全場已經被我的節奏掌握,彼此互動熱烈,從頭到尾聽完簡報。雖不敢說這是一場「成功」的簡報,起碼這已經註定不會是「失敗」的簡報。
我走下台,不知何時,莫圖也來到場,微笑地看了我的表現。他拍拍我的肩,用日語讚道:「侯桑,不錯。」
上午的考驗過了,進入中午休息時間。客戶為我們顧問公司人員準備了便當,我們就在會議室用餐。印度同事們吃不了日式便當,結伴到外面餐廳覓食,會議室內就剩我和對手OO公司的人員。我們禮貌性地閒話家常。OO公司的人好奇我的背景,彼此閒聊了一番。
「其實,我們身為日本人,也不愛做日本公司的案子。就算是到海外做也不樂意為日本公司做。」OO公司一名叫內藤的顧問私下和我這麼說。
「為什麼?」我問道。
「細かい(太瑣碎了),難搞。日本客戶的要求吹毛求疵不說,有時僅僅為了一個系統功能,比方說,單純做個『應收帳款管理』,客戶的需求不斷堆高,堆到最後,非得要幾個顧問一起來才勉強做得成。所以,可能的話,我們也想搶歐美客戶的案子。畢竟好做多了。」
「那倒是。」
「侯桑,多多指教了(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內藤深深地鞠了個躬,禮數周到地展現風度。
「哪裡哪裡,彼此彼此。」我也回了禮。
這類的話,我在台灣也聽過不少。論起吹毛求疵,可能日本客戶遠在台灣客戶之上。但論起何者「難搞」,則台灣客戶絕對不比日本客戶「好搞」。台灣客戶普遍樽節開支,一個系統案子,在七折八扣下,廠商彼此削價競爭,甚至到了影響系統品質的程度,是最大的問題。只是,成本可量化,品質難量化,當下省的錢,立刻反映在當年度的營收上;但犧牲掉的品質,往往多年之後才會嘗到惡果。

下午,進行另一個議程。客戶提出他們面臨的問題,希望從我們系統顧問得到解答。
「我們很想知道我們國家消費稅調漲到8%時,你們設計的系統有沒有辦法迅速對應?」
這是日本客戶會計部門的人員提出的問題。
講到日本的消費稅,就不得不提神仙也難救的日本「公債」。日本的公債是日本國民總生產毛額的兩倍。白話地說,等於一圓日幣的錢才賺到手,就得還兩圓日幣的債。用資產負債表來看,2012年底,日本共有負債1088兆日圓,資産總額卻僅有626兆日圓,幾乎是把整個日本都賣了也還不起錢。日本再不增稅,則國家何時破產都不奇怪。調漲消費稅是必走的路,但一次調漲太多,對經濟打擊面太大,所以日本政府計畫分段實施。第一次從5%調到8%,接下來再從8%調到10%。調到10%之後,是否就不會再調,誰也難預料。但每調一次,日本各公司的資訊系統就得更動一次,意味著我們系統顧問又能多賺一次。
OO公司的顧問似乎對此成竹在胸,立刻答覆道:「系統的更動相當簡單,只需把系統裡關於消費稅的設定,從5%改成8%就可以了。」
顧問說完,翻譯也說完,瑞士籍的專案經理滿意地點點頭。
我聽了一肚子狐疑,私下問了銷售系統專家瓦拉:「有那麼簡單嗎?」
瓦拉稍加思索,低頭小聲對我道:「當然沒那麼簡單,我在印度就改過。改消費稅的當下,未出貨的銷售訂單、未到貨的訂購單、退貨的發票,該維持舊稅率?還是新稅率?OO公司的顧問一個字沒提。侯桑,我們打回去!」
「瓦拉,有你的,你準備娶老婆吧!」我誇完他後,立刻舉手道:「對不起,我們想補充一點。」
專案經理看了我一眼後,示意讓我回答。
「村山首相決定調漲消費稅那年,我在日本念書,記憶猶新,因為他一決定要調到5%,就把我嚇回國了。所以算一算,5%的稅率從那時維持到現在,都十多年了,誰也不敢說自己有著豐富的『更改消費稅設定的經驗』,」我笑了一下:「包括OO公司的顧問也一樣,對吧?」
OO公司的人面面相覷答不出話。
「所以,我們有這方面經驗豐富的印度顧問。根據我們顧問的評估,系統除了要改稅率,還得掌握訂單和退貨,」我再加了一句:「這種事,得找真正有改稅經驗的外國顧問。可能日本經驗派不上用場。」
客戶的會計部經理像是恍然大悟,拍起桌子喊道:「なるほど(原來如此)!」
就這樣,下午的會,我們再度奪回主導權。我們對中國用戶解釋了中國企管系統的做法,對日本用戶說明日本特有的系統架構,一天下來,幾乎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以一個外籍兵團而言,我們算是表現不俗。會後,我和印度同事們相視而笑:「我們大概贏定了!」
這個信心,一直維持到第二天的上午。
急轉直下
第二天一早,我們來到客戶公司的會議室。這天下午要與客戶歐洲總部的全球專案負責人做電話會議。
OO公司的人早就到場,像是竊竊私語些甚麼,一看到我們出現,卻又停止了討論,氣氛明顯詭異。我沒放在心上。我把公事包放好,走到了茶水間倒水,見到OO公司的內藤顧問一個人在茶水間裡。
「どうも、こんにちは(您好呀)。」我禮貌性地打了個招呼。
內藤也回了禮,眼神卻有些飄忽。我邊倒水,邊聊些天氣等閒話。內藤附和了幾句後,看看周遭無人,突然壓低聲音對我說:「侯桑,我們查了…。」
「恩?查了?」我聽得一頭霧水。
「透過認識的人查了你以前的公司,知道了一些你的事。」
看著內藤的表情,我深知OO公司「查到」的,必然不是我的「豐功偉業」。
我當初為了和日本同事吵了一架憤而離職,這是我人生僅有的一次意氣用事。如果OO公司有心,大可以拿此借題發揮,「侯桑不合群」、「侯桑不勝任」…風評只需簡單一句,卻足以讓我百口莫辯。顧問業界是個封閉的圈子,具備了壞事傳千里的所有條件,換成日本也一樣。
我依稀想起內藤昨天和我閒聊時,是邊談話邊抄筆記的。當時只暗自笑日本人迂,連閒聊也要「記重點」,這下全明白了。
「對不起,昨天公司都知道我和你聊了天,所以,從我這裡探聽了一些你的事情,再透過認識的人問到你以前的公司…。」內藤說時帶著慚愧,表情像極了日本電器行裡為了「商品缺貨」向客戶道歉的店員。只要稍加訓練,任何日本服務業從業人員的表情都能做出這樣專業的「愧色」。
「いいえ、いいえ(沒事沒事)」我故作鎮靜道:「この業界って狭いっすね(這圈子真小呀)」。
我胡亂說了幾句應酬話後,就匆匆走出茶水間。
「侯桑,」突然內藤從背後叫住我:「你倒的水忘了拿走!」我回頭,勉強擠出笑容,轉身去取我的水杯。「侯さん、大丈夫?(侯桑,沒事吧)」內藤追問道。我連聲「はい(是的)」之後,離開了茶水間。
現在就斷定內藤是敵是友,尚嫌過早,但就「擾亂軍心」這一點來看,他的目的確實達成了。接下來的議程,我如同洩了氣的皮球,客戶的問答我都聽得左耳進右耳出,客戶感受到了,我的團隊更感受到了。我必須承認,我實在不具備談笑用兵的資質。商場就是戰場,OO公司沒有對我手軟的道理,想到這一點,我的樂觀情緒完全消失。
「侯桑,」瓦拉關心地問:「Are you alright?」
我回過神,強打起精神,還是重複那句話:「你只要把老婆顧好。I am alright.」
這是色厲內荏了。他顧老婆,誰顧我?看著OO公司的顧問不時與客戶專案經理交頭接耳,對此刻的我而言,全是磨刀霍霍,杯弓蛇影。我極可能被這個專案掃地出門,莫圖對我的信任自此瓦解,我在這個業界再無立錐之地…。I am not alright!
休息時間,莫圖不知何時出現在我面前,把我叫到另一個小會議室。
「侯桑,…」莫圖和我對坐,欲言又止了半晌,結果還是開了口:「there are some discussions going on(我們正在談一點事)」
「甚麼事?」我問道,但幾乎猜到八分,心裡已經做了最壞打算。
「我猜客戶大概從別處聽來甚麼了。客戶說,…客戶說,如果侯桑代表我們公司主持這個專案,他們可能無法與我們合作。」
果然,這是我能預想到的最壞狀況,莫圖親口說出,算是利空出盡了。
「但是,今天的會總要開。我和客戶說了,關於侯桑,我們會另外安排。你別消沉,下午你還是代表我們把會開完吧。」
我點點頭答應。氣早就洩得差不多,莫圖的話更讓我一路洩到底。翻盤沒可能了,下午是和客戶歐洲總部專案負責人的電話會議,電話會議完,我就被請出專案。我成了個道地的瘟神。
下午,我有一搭沒一搭地開著會,幸虧內容不是那麼重要,也可能是我自動「視為」不重要。就這樣熬到了三點,正式與歐洲全球專案負責人開始電話會議時,卻遇到了我生平最戲劇性的一刻。
全球專案負責人,彼特(Peter),是個很容易記的名字。生平已不知道遇過多少彼特,洋人彼特與華人彼特。透過會議室的電話會議設備,彼特和大家親切地打招呼。
「大家好,KONICHIWA(日語的「你好」)。」
「嗨,彼特好!」
「你們該是下午了吧?我們這裡是早上。」
「是的,我們是下午。你剛睡醒?」瑞士籍的專案經理促狹道。
兩人寒暄了一下之後,彼特突然話鋒一轉:「侯桑在嗎?」
會場的目光全投向我。我今日的表現與昨天完全不同,幾乎沒做過一句發言。聽到叫喚我的聲音,我像是醒了一般,繃緊了神經,應了一聲:「Yes!」
「侯桑,你忘了我了?我是B集團的彼特!」
B集團?我在回憶裡翻攪一番,總算想起了這個荷蘭籍「B集團的彼特」。我精神大振,起身快步走到電話會議麥克風旁道:「Hi, Peter, how can I forget you!!(彼特,我當然沒忘記你)」
在離開前一份工作○○株式會社前,我曾與其他同事被公司派到這家歐洲「B集團」東京分公司,擔任他們系統更新計畫的顧問。彼特就是當時「B集團」這個專案的負責人。我們人馬浩浩蕩蕩進駐了一天,就被告知「B集團」因為去年財報結果出現大幅赤字,今年必須節省開支,「系統更新的計畫無限延期」。這個消息正是由彼特發電子信告訴大家的。
僅僅待了一天,就被告知收攤,大家都覺得錯愕。我還記得當時同事們彼此苦笑,收拾打包的情景。
當時,我突然想到一個主意:「發個信給彼特,給他打打氣吧。」為此,我和我們的專案主管提了一下。
「余計なことしなくてもいい(別沒事找事),」專案主管一句話就把我否決了:「這是業務人員該做的,不是你做的。」
話雖如此,我還是在事後偷空發了電子信給彼特,信中除了對他們B集團的狀況感到遺憾之外,我還這麼激勵他:「我相信我們會在東京再見面!」
這是將近一年前的事情了。我只知道後來彼特也跳了槽,但萬萬沒想到彼特現在在這家客戶做起了全球企管系統負責人。
「侯桑,你說中了,我們又在東京見面了,呵呵!」彼特說著,兩人光是敘舊就談了五分鐘,其他會議出席者好奇地看著我和彼特的交談,完全不知道我和這位「全球系統專案負責人」之間有著甚麼淵源。
這個專案後來花落誰家,不須我多做交代了。瓦拉下個月就要結婚(比預計延期了);山繆爾則早買了摩托車;而我也總算在東京有了一筆遠高於一般上班族的收入。
彼特事後和我聊天時,這麼說著當時的心情:「B集團說要縮緊預算,接著就是裁員。我對你們公司很抱歉,但我自己也是惶惶不安,因為自己可能就是裁員對象之一。」彼特描述的狀況,完全在我的想像當中。若非公司財政惡化、必須採取斷然措施,一般來講,這種毀棄商業契約的事情,是不太可能做的。B集團當時必然遭遇大變。
「在這種狀況下,侯桑,你發的那封mail,確實讓我看了很受用。一封鼓勵我的信,居然是來自外部顧問,你們的銷售業務都沒那麼貼心。呵呵。」彼特笑了笑,接著說:「日本人做事很守規矩,但你做事很講感情。一個講感情的人,是不可能丟下客戶不管的。這個專案我要定你了。」
這是我在異鄉商場的第一仗。如今想想,還是充滿了太多的不可思議。所謂「交友須帶三分俠氣,做人要存一點素心」,這是我們華人最樸質的做人基調,連翻成外文都難,卻在意想不到的時刻、意想不到的地方,發揮了不可思議的力量。
做人,不就是那麼回事嗎?
就這樣,我又重回到每日擠電車的日子,您下回若來東京,看著「滿員電車」,遠觀可也、訕笑可也、照相可也,若在壅擠的人群中,碰巧看到一張擠得變形的笑臉,呵呵,那多半是我了。
●作者老侯,碩畢,在日本謀生的台灣上班族。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讀者迴響